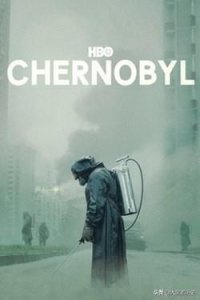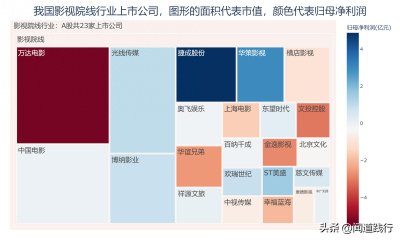黄庭坚《松风阁》诗书共赏
武昌松风阁
黄庭坚
依山筑阁见平川,夜阑箕斗插屋椽。
我来名之意适然。
老松魁梧数百年,斧斤所赦今参天。
风鸣娲皇五十弦,洗耳不须菩萨泉。
嘉二三子甚好贤,力贫买酒醉此筵。
夜雨鸣廊到晓悬,相看不归卧僧毡。
泉枯石燥复潺湲,山川光辉为我妍。
野僧旱饥不能饘,晓见寒溪有炊烟。
东坡道人已沈泉,张侯何时到眼前。
钓台惊涛可昼眠,怡亭看篆蛟龙缠。
安得此身脱拘挛,舟载诸友长周旋。
黄庭坚《松风阁诗帖》墨迹,后人誉为天下第九行书
依山筑阁见平川,夜阑箕斗插屋椽。
“箕斗”,星宿也,竟“插屋椽”,故知“依山筑阁”之高。所谓登高作赋,人居高处,俯仰天地,神接造物,中有所动,故发而成诗。开篇写自然而极自然。
我来名之意适然。
中有所动者,“适然”是也,看似平平道来,实则全篇基调已定。
长枪大戟,而整体有精美清旷之感
老松魁梧数百年,斧斤所赦今参天。
松风之“松”在此。
人皆赏其“赦”。意不独在状树,更在自述 ,有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之磊磊傲气。
风鸣娲皇五十弦,洗耳不须菩萨泉。
松风之“风”在此,“我来名之”松风阁,松风次第交代,自首句下,承接有序,知山谷作诗从容,大家风度。
风起松涛,自然之声也,“娲皇”者仙,“五十弦”者乐,所谓“如听仙乐耳暂明”者也。
“洗耳”用典:尧欲禅位许由,告之,由以帝位为秽,闻则污耳,故洗耳。
许由之举,有做作之嫌。接自然而心澄明,俗世污秽,自不入耳,何须洗?所以在许由之上。
字或大或小,或长或短,或收或放,疏密相间,穿插争让
嘉二三子甚好贤,力贫买酒醉此筵。
“力贫”难碍“买酒”,既得酒,必“醉此筵”。人生唯二三知己难得!
“佳三二子”,笔误,“乙”状符号示意顺序颠倒,不讳错字,也见性情
夜雨鸣廊到晓悬,相看不归卧僧毡。
此句尤要紧:何以知“鸣廊”,诗人应不眠。
遭贬黔戎,所谓“万死投荒,一身吊影”,今虽得复用,然九日即罢,是以暂住武昌(诗题《武昌松风阁》),前途渺渺,凶吉未料。
念及昨日之迫害打压、忧愁困苦,今日之“二三子”、“醉此筵”,苦乐交织,世事茫茫,“不如意事常八九,可与语人无二三”,念及此,岂能眠?
然雨终夜,万籁寂,但闻淅沥,或有松涛。山谷有句:“清风明月无人管,并作南楼一味凉”,最宜作注。“一味”多以饰药,化清风明月为药,真新奇语!此药医何病?正是前文之愁肠百结。
泉枯石燥复潺湲,山川光辉为我妍。
“泉枯石燥”不独为实景,一夜雨润,亦润人心。
“山川光辉为我妍”为全诗最佳,山川者,即松风,即清风明月,皆谓造物者也。
东坡《赤壁赋》: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
山川光辉,为我所得,即为我一人独妍,何等胸怀,何等心态。山谷随东坡,陷于政敌迫害,流放贬谪,且刻名于“元佑党人碑“,竖于端礼门外,以示“永不录用”,劳苦倦极,所谓“泉枯石燥”者也。
屈原言,“劳苦倦极,未尝不呼天也”,中有凄苦意。山谷不然,于劳苦倦极处通天,有适然旷达意,且意境宏大,深得东坡风神。
“旱”误作“早”,点三点以示删去,《兰亭序》《祭侄稿》《寒食帖》三大名作皆有涂改,是以真性情成就艺术
野僧旱饥不能饘,晓见寒溪有炊烟。
“野僧旱饥”,“饘”者稀粥也,尚不得食,此天灾耶?人祸耶?是非难辨,但知政治斗争不独困厄士人,亦苦天下苍生。
身在江湖而心忧天下,又是一种情怀。
然今见“炊烟”,旱饥者得食,生机所在。
东坡道人已沉泉,张侯何时到眼前。
炊烟袅袅,随风烟去者,苏轼是也。作此诗时,东坡已沉于九泉之下,此一憾也。张侯者,友人张耒,同属“元佑党人”,贬谪难见,又一憾也。人生挚友本寥寥,今逝者故不可见,欲见存者而身不由己,天地悠悠,感慨万千。
整篇典型中锋用笔,字更圆润饱满但结体依然偏向瘦劲,转折之处也比早年更加缓和
钓台惊涛可昼眠,怡亭看篆蛟龙缠。
“钓台”,孙权昔日畅饮处,“惊涛”尚能“昼眠”,纷纭难乱适然心。“怡亭”,书家李阳冰挥毫处,字如“蛟龙”,赏其俊逸不拘。
所谓“意适然”,这些舒展的长笔画,是否正是心灵舒展的外显呢?
安得此身脱拘挛,舟载诸友长周旋。
于“钓台怡亭”之逍遥处,难不念及自身处处受掣肘,俗世拘挛,“安得”脱逃,欲得一小舟,但载友人,游于江湖,作“长周旋”。
总结
“适然”纵为全诗主题,然读此诗,不适之意其实终究萦绕字句之间。末句“安得”,反生发出“而今偏偏不可得”之怅然。山水之幽静,似可隔绝世俗苦难并安放自在心灵,故失意之士人,多有所寄托,然一定能化解吗?
司马光,苏轼,秦观,黄庭坚,张耒等人名字皆在其中
有人诟病山谷此诗,无非是“消极的道德自我完善”,未免过分苛责。诗中求适然而每感不适,恰是能见其本来处。所谓“流连山水”,山谷唯游之以疗伤,不曾玩之而沉溺,与其掘其“消极”,不如赏其“积极”。

黄庭坚纪念馆
主政泰和期间,山谷整吏治,抗盐税、察民情,百姓称之为“黄青天”。所留“当官莫避事,为吏要清心”“不以民为梯,俯仰无所怍” 等句,朴实致诚,又能躬身行之。其人岂独意在山水?
初读柳宗元《永州八记》,不解其意,以为其游记凄冷而胸中郁结未解,终不快意,非游记之佳作。后见其人生平,方知其意固不在山水,所谓“二王刘柳”,“永贞革新”,出入政坛者,倘若得志做文书,治天下,岂有心玩山水,工游记耶?
所以所谓佛老思想的“消极之处”,恰恰是与儒家开拓进取之精神互补的。
人生在世,既要谋求事功,又要修身养性,既能居庙堂之高,也能处江湖之远。
这便不再是所谓非此即彼,有你没我的两端,恰恰是二者中和之后,早已融入中华文化核心之中的精神。